文明肇啟 壯闊史詩
北緯43°25′55.00〞,東經120°46′45.3〞,西拉木倫河流淌到這裡,與迎面而來的老哈河深深相擁,手挽手向東而去。
靜水深流,潤澤蒼生。匯流而成的西遼河從歷史深處走來,穿沙辟石百折不回,舒緩中時見激越,輕靈中飽含凝重。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在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大約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
農之伊始 禮之肇端
驅車沿111國道從通遼市區出發,一路上是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遍野金黃,收割機、運糧車在田間地壟來回穿行。
一座充滿歷史真實感與滄桑感的建筑由遠而近矗立眼前——那是內蒙古哈民考古遺址公園。
哈民遺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是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北緯43°以北地區,首次大面積發掘的保存最完整的史前聚落遺址。
“這是‘中華史前第一美陶豬’。”哈民遺址服務中心主任董哲指著展櫃中一隻身體蜷曲、造型生動、黑褐色的陶豬說,“它的肚子裡裝著碳化了的粟黍。”
植物考古專家、赤峰學院副院長孫永剛曾於2012年至2013年,對哈民遺址進行了採樣、浮選和種屬鑒定工作,共出土黍、粟和大麻3種農作物種子合計638粒。
浮選法為探討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在興隆溝第一地點浮選出土的8000年前的碳化粟和黍(小米和黃米),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谷物,從而進一步推斷西遼河上游地區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地之一。”孫永剛說。
“故人具雞黍”“春種一粒粟”,雖然在現代人的餐桌中,黍已經十分稀罕,粟也沒有像小麥、水稻、玉米那樣成為人們的主糧,但是在古代典籍和詩歌裡,它們出場頻率極高,在中國傳統農業的“五谷”裡,更是妥妥的“大哥”地位。
著名文化學者許嘉璐先生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幾個根基點,基本上都立足於原始農業社會對人的要求,對人的品德的要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炊煙裊裊、一餐一飲中,“天人合一”“和諧與共”“福禍相依”“遇變不驚”“和睦相處”“艱苦奮斗”等由原始農業孕育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根基,開始鐫刻在基因和血脈裡。
西遼河流域大約在8000年前開始了文明起源的進程。原始旱作農業的發生,是其中一個重要標志。
如今的西遼河流域仍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今年,哈民遺址周邊的玉米喜獲豐收。“玉米灌漿期的水肥管理對於最后的高產豐收至關重要。現在運用的是無膜淺埋滴灌技術,與普通漫灌相比,能節水70%左右。”科左中旗水務局副局長楊昭武說。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感恩大自然的饋贈,在西遼河畔,古今攸同。
生活在西遼河畔史前先民,安靜凝望那日升月落、風雨雷電的萬象,冥思苦索那山川相繆、草木枯榮的變化,努力生長,創造了興隆窪、趙寶溝、紅山以及小河沿等近萬年來傳承有序的史前文化,與山河輝映。
把視野放大,會發現,“中國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西遼河文明始終貫穿其中。”內蒙古民族大學教授、西遼河文明研究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張鐵男說。
那是距今5800年至5200年間,在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紅山文化的發展達到頂峰。
我們仿佛可以看到,高山、台地、祭壇。熊熊篝火與點點星光相映,紅山王巫緩緩前行,登得越高,越靠近蒼穹。他手中的玉龍,在暗夜裡閃耀著靈動。
唯有王巫可以溝通天地。“得天地之精”的玉石等稀缺資源、天文歷法等神秘知識、喪葬祈福等祭祀禮儀,一概掌握在王巫手中。
此時,中華大地“古國”紛紛涌現,“滿天星斗”競相閃耀,古國間存在遠距離的文化交流。
“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都是交流的內容。” “這樣的交流催生了一個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歷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蘇秉琦提出的‘共識的中國’已經出現,費孝通論述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初步形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在《考古學証實五千年文明史》中說。
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國祥認為,哈民遺址是僅次於牛河梁遺址的埋葬與祭祀中心,哈民陶豬“跟龍的圖騰的崇拜有密切關系,為了祈求農業生產的豐收。”
龍,中國人之間最親切的身份認同,最早便騰起於西遼河文明。
從興隆窪文化時期軀體用石塊和陶片擺放的豬首龍,到趙寶溝文化時期尊形器上刻畫的、頗有宏大氣魄的“豬首靈”形象,再到紅山文化時期的C形玉龍、玉豬龍……
龍文化在遼西地區具有連貫的發展脈絡。西遼河流域的史前先民們人為地規范了龍的構形理念,並傳承后世。這樣由幾種動物復合而成的形態也與中華多民族的大融合交相呼應。
蘇秉琦先生談構成民族特性的傳統精神時講到:“玉代表了一種崇尚高潔、堅貞、溫良的美德,體現著中國傳統的道德標准、價值觀念。”
8000多年前興隆窪文化以軟玉為主體的玉器橫空出世,代表了中國真玉文化發祥的肇端。紅山文化時期將審美價值、思維觀念等注入玉器之中,並賦予了玉器規范、禮制等濃厚的人文思想觀念,開啟了中國祭祀類玉禮器的先河。
從“以玉為美”到“以玉為貴”再到“以玉為禮”,西遼河文明史前時期完整體現了這一過程,為“以玉比德”奠定了基礎。
交流持續。龍的構形理念、玉的禮制規范等西遼河地區最先進的文化精粹不斷在各“國”間傳播、交流、互動。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
在堯都平陽(即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斝、鬲、彩繪龍紋盤,以及彩繪、朱繪黑皮陶器都包含了紅山文化因素。
遼寧省文物保護專家組組長、遼寧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郭大順先生指著紅山文化南下和仰韶文化北上的交匯示意圖說:“紅山文化在強勢時向無阻隔的東北鄰區推進少,而以越燕山南下為重點,這是紅山先人的歷史使命感所為。”
西遼河文明不斷向中原匯聚。
距今約4000年至3500年期間,西遼河流域分布著夏家店下層文化。從中原地區吸收了青銅鑄造技術、流行在丘陵地帶以石塊修建山城,墓葬反映的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西遼河進入方國文明社會,加入中華大地“萬邦林立”的政治景觀。
風雲際會 合而為一
鼓點雲鑼。皓首白須的老將黃忠手握金刀,銀須飄搖,跨上戰馬,將一把寶刀舞得密不透風。
這是一曲定格在西遼河畔的《定軍山》。
在通遼市庫倫旗象教寺玉柱堂,繪制著《定軍山》《斬馬謖》《趕三關》等中原戲曲故事,余韻悠悠,慢慢沉澱為西遼河流域永不磨滅的集體記憶。
蘇秉琦先生把西遼河流域比喻成精彩的舞台,“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集中地反映在這裡,先秦前如此,就是以后,‘從五胡亂華’到遼、金、元、明、清許多重頭戲都是在這個舞台上演出的。”
西遼河流域,是多民族雜居之所。燦若星河的文物遺跡講述著各民族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通遼市博物館研究室主任姜子強指著一件青銅器說:“這是西周時期邢國的青銅禮器,它是在通遼市霍林河畔發現的。這裡是目前我國出土商周青銅器的最北點。”
“邢姜太宰巳簋”,雙耳圈足,精美庄重,饕餮紋、夔龍紋,繁復的紋飾,營造了神秘莫測的氛圍。
龍首魚身、欲展翅跳躍的遼三彩摩羯壺,釉色斑斕、舒朗清爽,運用的是中原技法。
紫定印花碗,釉色柔和,瑩潔可鑒,花紋精美,井然有序,是宋瓷定窯出品。
“這是度量衡中的量,秦陶量。”姜子強說,“它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的詔書量器,是秦代在全國統一度量衡制度的有利依據,也為研究秦代對邊疆治理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秦,大一統,早已深深鐫刻於中華民族的血肉骨髓之中。提起,則熱血沸騰。
“其實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意識更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時代,那時以華夏族為核心的文化圈基本形成,奠定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治基礎。”張鐵男說,“秦漢時期國家形式進入帝國階段,中華文化圈有了一個統一的、強盛的國家形式,中華民族的雛形漸成。”
“對中華民族形成起決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對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華文明’的認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蓋之庸說。
吉林大學教授趙永春在《中國認同:邊疆民族與內地民族“統一性”研究》一文中作了如下梳理:“拓跋鮮卑建立北魏,以黃帝之子昌意少子為自己的直接祖先,以‘炎黃子孫’自居。”“遼在自我認同為炎黃子孫的同時,又按‘五德終始’的正統學說,以繼承后晉水德的木德自居,將遼王朝排列到后晉之后的中國正統發展譜系之中。”“金章宗‘更定德運為土’。”“元還遵循中國古代為所滅之國修史即是認同繼承其法統的傳統觀念,按照遼、宋、金‘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的編撰體例,修成了中國正史《遼史》《宋史》《金史》。”“清建立起一個包括漢、滿、蒙、回、藏等的大一統王朝, 中華民族正式形成。”
“可以說,西遼河文明是多民族共創中華的實証,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活標本。”蓋之庸說,“在西遼河流域,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盡管有戰爭,但‘合’是主流。澶淵之盟后,宋遼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保持了長達100多年的和平狀態。”
山河一統、安享太平,是中華民族刻入骨髓的終極追求和美好憧憬。“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平共處”等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精神中,深深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人們渴望和平、珍視和平,也敢於用斗爭去捍衛和平。
融通互鑒 守正出新
如果鳥瞰西遼河流域,就會發現它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
它位於蒙古高原、華北平原、東北平原三大地理板塊的接合部﹔就世界范圍而言,屬於歐亞大陸草原通道南緣東端,瀕臨北太平洋西岸。
這意味著古代的西遼河流域處於連接中國南北和溝通世界東西的交通要沖。
“這裡是交通的‘大驛站’,文化的‘大熔爐’。”蓋之庸說。
“體現交通‘大驛站’性質最典型的是陳國公主墓。”奈曼旗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中心主任周偉東說,“陳國公主墓是迄今為止出土規格最高的遼代貴族大墓,出土了超過3000件隨葬品。其中,瓷器是中原的,琥珀是波羅的海地區的,玻璃器皿是西亞的。”
將時間軸拉長。
“距今4800年至4000年的南寶力皋吐遺址多種文化因素十分突出,除了自身特色鮮明的陶器外,還發現了小河沿、偏堡子、嫩江流域類型陶器。”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吉平說。
由眾多涓涓支流匯聚而成的西遼河,塑造了西遼河人民開放、包容的文化品格。
郭大順先生認為,“‘兼收並蓄’是西遼河文明發展和傳承后世的主要動力。”
“這裡不只是‘通道’,西遼河文明更注重‘化’的功夫,就是把外來文化的強勢因素,進行‘本土化’改造,進行創新。”蓋之庸說。
用歷史的長鏡頭來看。
紅山彩陶匠人在紅陶罐上精心勾勒,經過火的淬煉,一款兼有龍鱗紋、中原玫瑰花紋和中亞菱形方格紋的彩陶新品橫空出世,引領時尚﹔
遼太宗為選天下之才辦天下之事,統領著各民族社會精英,以極其務實和創新的態度,建立北南面官制,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典型的最早的制度創新﹔
還有留在如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醇香的奶茶、火熱的安代、吟唱著的烏力格爾……
文明的交流是相互的。西遼河文明在吸納其他文化優秀因素的基礎上,也在深深影響著其他文明。
述往事,思來者。
站在西遼河畔回望,無數文明記憶奔涌而來。
綿延不斷、博大精深、歷久彌新的西遼河文明,成為我們接續奮斗、逐夢奔跑的底氣所在、信念所在、活力所在。
從高空俯瞰,會發現,引綽濟遼工程宛若一條藍色的哈達,以群山為側顏,穿越蒙東大地。
西遼河正以海納百川的胸懷,跋涉奔流,福濟蒼生。
壯哉!西遼河!(記者 李倩 郭娜)
(內蒙古日報社、中共通遼市委宣傳部聯合推出)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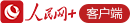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