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子溝聚落文明探源


廟子溝聚落遺址。


發掘現場圖。


廟子溝遺址出土的彩陶雙耳壺。


出土的石器。
1985年的秋天,一位在內蒙古察右前旗新風鄉磚窯打工的中年男子,走進了察右前旗文管所的辦公室。這位操著山東口音的農民工稱在廟子溝村南的山坡上取土時,發現了很多的石器、陶片和人骨遺存。由此,廟子溝這座塵封了5000多年的原始聚落遺址揭開了神秘面紗。
“廟子溝遺址經過1985年至1987年連續三年的發掘,呈現出了一個保存相對完整的原始村落遺址,為人們了解新石器時代晚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文化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一直主持廟子溝遺址發掘、時任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中國人民大學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魏堅教授說。雖然廟子溝村只是一個荒蕪的小山村,但廟子溝遺址,在中國考古學界史前聚落研究的行列當中,有絕對的知名度。
聚落遺址保存相對完整
廟子溝遺址位於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的黃旗海南岸丘陵地帶,經考古發掘研究和碳14測定証實,遺址距今約5500年至5000年間,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掘面積最大、遺跡保存最完整、出土遺物最為豐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址。
對於聚落遺址發現經過,當時擔任察右前旗文管所所長的天津知青孫家譚在其《回顧“廟子溝新石器聚落遺址”發現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詳盡描述。孫家譚在看了山東來的農民工拿來的“石磨盤”后,當即叫上所裡的同事羅錦明直奔現場拍照、收集遺物,並立即將掌握的情況報告了當時的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5年10月10日,魏堅被指派前往廟子溝遺址進行現場考古勘查,魏堅說,當時和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同學郭治中乘坐一輛212吉普車到了廟子溝村,在確認了遺址的文化性質后,隨后就組織了考古發掘。
在魏堅看來,廟子溝遺址東接張家口,西連鄂爾多斯地區,南部就是山西、河北,過去在這一區域沒有發現類似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遺址位於廟子溝村南,第一次發掘大概持續了15天左右,從發掘現場看到的人骨和出土文物感覺應該是一種墓葬的隨葬品。”在魏堅的印象中,1986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將該遺址記錄為廟子溝新石器時代墓地的認識有誤。“事實上,它不是一處墓葬,而是一座史前村落遺址。”進入1986年,魏堅對廟子溝遺址進行了近三個月的大面積發掘,發現廟子溝遺址既有房址、灰坑和窖穴,同時也有墓葬。1987年5月至9月間,進一步通過大面積布方的方式進行發掘,對遺址進行了全面揭露。
發掘結果表明,廟子溝遺址共發掘房址50余座,灰坑、窖穴130余個、墓葬40座,出土復原各類陶器700余件。陶器多小口雙耳罐,也有筒型的盛放器和用於煮飯的炊器。出土較完整的石器、石環、玉器、蚌螺串紋裝飾品等千余件,遺址內村落布局井然有序,房址成排,坐西朝東分布。制作精美的彩陶器、筒型罐和磨制精致的石器、骨器和裝飾品等均具有一定的工藝水平,文化面貌獨具特色。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陶器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陶器具有一定的區域特性,陶制筒型罐作為內蒙古東部文化遺存,從東北地區經黃旗海的廟子溝遺址,向西到鄂爾多斯地區,在連接西北地區的馬家窯遺址的整個區域均有發現。廟子溝遺址出土的筒型罐、彩陶罐、夾砂罐、偏口器等器物,構成了一個器物群的考古學文化,証實距今5500年左右,區域間文化交流非常繁盛。魏堅認為,這種陶器組合既可以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又表明相互之間存在聯系,體現出了“多元一體”的格局。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北方,直至夏商時期,存在著風格各異的眾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猶如“滿天星斗”。最終,眾多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屬仰韶文化晚期遺存
已有的考古發現証實廟子溝遺址的年代與陰山以南包頭阿善遺址、黃河大回折托克托海生不浪遺址一樣對應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至5000年之間,廟子溝遺存涵蓋了阿善、海生不浪因素,屬於仰韶文化晚期遺存,是一個單獨的文化類型,魏堅在對廟子溝出土文物進行整理和研究過程中,逐漸有了新的認識。他說,距今5500年這個階段,相當於中原的半坡四期考古學文化階段,廟子溝文化在這個階段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北方地區一支新型的考古學文化。
廟子溝出土的大型生產工具如磨盤、磨棒等,為數眾多。同時出土了一件帶有穿孔的形制獨特的石鏟。魏堅分析,這件石鏟極有可能是部落首領權利的象征。在探討中華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的時候,有著某種象征意義的石鏟是一個重要的佐証。以內蒙古中南部的廟子溝遺址、阿善遺址、海生不浪遺址為代表的三個區域類型,彼此年代相當、文化面貌相同、分布區域接近,魏堅將其命名為廟子溝文化。廟子溝文化區別於仰韶時期的其他考古學文化,具有獨特性。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中,重點強調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域、發展系列和不同類型的問題。每個區域都有一個系列,每個系列當中都有自身獨特的類型。魏堅在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各種石環的半成品,他認為,墓葬裡人骨的手腕上戴有石環的一定是女性,兒童一般胸前佩戴玉片和一些從黃旗海捕撈的蚌螺制成的飾品。遠離黃河流域的廟子溝原始聚落,同中原地區中華文明的其他聚落一樣,在距今5500年左右,已經開始向文明邁進。
大范圍文化交流現象,從一個側面証實距今5500年左右這個階段是中華民族文明產生的前夜。“解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解讀史前文化發生發展和繁榮的過程,廟子溝文化的存在非常有價值,不可或缺。”魏堅說。
魏堅從1985年進入廟子溝到2004年離開,20年的歲月裡,魏堅一直堅守在廟子溝,他第一次去廟子溝時,兒子出生,離開時,兒子考上了大學,魏堅堅持不懈對廟子溝遺址出土的資料進行深入研究。他坦言,通過考古學展示,人們有了認識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更多渠道。
為了查明廟子溝史前古人類的生活生存狀態,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學者劉莉教授等人曾經從廟子溝遺址出土的磨盤、磨棒上提取植物澱粉進行鑒定,証實食用植物主要為粟和黍,同時,通過對發現的人骨進行同位素測定,也証實食用植物為粟和黍以及糜子。此外,對發掘出土的40多種動物骨骼進行鑒定,証實有牛、羊、馬鹿、黃羊、狍子、熊以及家養的豬、狗和少量水生動物。另外,在每個房子西側的正中央,在灶坑與牆壁間有個地臼,底部和側面用泥和石子硬化,用來搗碎採集到的堅果類食物。
在生活場景裡,廟子溝的先人在山坡的丘陵上打獵,在附近的黃旗海捕魚,同時採集野生果實,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當時完整生動的生活場景。
深挖文化內涵
廟子溝遺址發掘現狀表明,廟子溝原始聚落的人們在5000年前突然毀滅並神秘消失,這一現象一度在考古學界引起震動。
按照考古學的表述,廟子溝遺存與內蒙古東北部的紅山文化以及西部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構成了一個文化發展脈絡上的三岔路口。而廟子溝遺址與其他同時代遺址展現的最大不同,是居住址內發現有大量的人骨,這些人骨在房址和窖穴中既有專門的擺放,也有隨意的丟棄,有多人合葬,也有兒童和成人合葬。這些現象能夠揭示廟子溝原始聚落突然消失的謎團。
盡管廟子溝遺址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文明,然而考古學者卻發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魏堅在發掘中發現,廟子溝遺址及周邊並未發現墓地,所有的埋葬都在居住址內的窖穴、灶坑以及居住面上,長方形坑內常有多人合葬的現象,有的合葬墓內尸骨擺放整齊,有的雜亂無章,這樣的尸骨擺放方式,顯然不符合常理。
大量的遺物、遺跡表明,廟子溝原始聚落極有可能在一場突發性災難中毀於一旦。根據魏堅的描述,有一處多人合葬的墓,尸骨雜亂地堆放在一起,直觀上看就是匆匆忙忙扔進去的,據此,對於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魏堅推測,遺址中既沒有水災的痕跡,也沒有被火燒過的印記。在排除水災和火災的可能性后,魏堅想到了部落戰爭以及地震、雷雨等天災人禍?但尸骨經過鑒定沒有任何砍殺傷。另外,遺址的所有房址裡,有一半的房址沒有器物、沒有人骨。有人骨的窖穴、灶坑以及居住面,生產和生活工具齊全,而沒有人骨的房址裡,也沒有生產和生活用具。在這種情形下,一個科學的推斷是:當時還活著的人將死者匆匆埋葬,帶著生產生活用具進行了遷移,這個現象証明當時當地發生了大規模的“瘟疫”。
魏堅推測發生的“瘟疫”可能為鼠疫。可能是一場鼠疫導致廟子溝原始聚落突然毀滅和消失。他說,在尸骨的底部可見很多鼠洞,尸骨的殘缺部分被老鼠拖進了鼠洞。曾經生活在廟子溝原始聚落的古人在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完整的生活場景后,就這樣突然消失了。
廟子溝原始聚落的消失,留給了后人無盡的遐想。內蒙古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用實物証實了內蒙古中南部自有人類繁衍生息以來,就是多文化、多人群的融合之地、交流之地。不同群體文化現象反應出的不同族群的面貌遺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創造的。考古學者們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並揭示了早期人類血脈相通相互交融的歷史脈絡,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魏堅建議應加強廟子溝遺址的保護力度,推動廟子溝原始聚落生活、生產場景的恢復,讓更多的人了解新石器時代晚期廟子溝遺址的文化內涵,讓更多的人去探究尋找中華民族文明史的光芒,從而樹立文化自信,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王林喜)
(本版圖片由察右前旗文物保護中心提供)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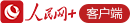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