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戰瀚海八百裡(山河志)

治 沙 圖片由AI生成
科爾沁草原,19世紀以來逐漸蛻變為科爾沁沙地,號稱八百裡瀚海,成為中國四大沙地之一,不免令人嘆息。科爾沁,意為金箭,原屬成吉思汗胞弟哈薩爾后裔部落游牧之地。
地處祖國廣袤北疆,這裡是國家重要的生態屏障,保護它的自然環境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過去一年,我們驅車千裡,輾轉深入科爾沁沙地治理第一線,見証了一場氣勢磅礡的沙漠大會戰。
一
位於科爾沁沙地庫倫旗中心地域的敖倫嘎查,是一個隻有60多戶的小村落,地處令人談之色變的塔敏查干流沙帶北側沙坳裡。塔敏查干意為地獄白沙,之前這裡幾乎被滾滾流沙吞沒。敖倫嘎查當地人常年啃沙坨子,廣種薄收,曾是有名的貧困村。2000年后,旗政府搞生態移民,遷走不少人家,並對周圍沙地進行生態治理,情況有所好轉。這幾年,國家推動實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簡稱“山水工程”),敖倫嘎查1.2萬畝沙地被納入這一工程。這是一次歷史機遇,給當地帶來了轉變命運的契機。
越野車在荒坨子裡七拐八繞,在一片新栽上錦雞兒、山杏的沙梁上,我們尋到了敖倫嘎查黨支部書記鐵山。一個高高大大的漢子站在眼前,50多歲,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風吹日晒常年勞作,他的一張紫紅臉上,皺紋如刀刻一般,微駝的身板則像沙梁上的老榆樹般有力。他正帶領幾名護林員巡視所屬“山水工程”地帶,剛好下過雨,看看春天栽種的灌木幼苗成活率情況。他撫摸一棵兩尺高的錦雞兒,欣慰地說:“瞅瞅,這棵新種的阿拉坦根娜,都長這麼高了!”
阿拉坦根娜?不是叫檸條或錦雞兒嘛?對我的疑惑,鐵書記笑呵呵地答復:“是的,但我們喜歡叫它阿拉坦根娜,意思是金子般的草。它是一種多年生灌草,根須密集,能扎進沙土裡幾米深處吸水,牛羊也愛吃,平茬兒后可做青儲飼料,從根部還能再長出新一茬兒。”我們感嘆真是好名字,金子般的治沙植物。另一側新栽的山杏也正綠油油地風中搖擺。鐵山介紹,“沙化之前這裡漫山遍野都生長著山杏、山楂樹、桑椹、榆樹毛子、麻黃草等植物,后來荒漠化嚴重,加上人砍牲口啃,肆意掠奪,如今都消失了。我們現在的策略是,沙坨子上原先有過什麼就恢復什麼、種植什麼。早先的生物群落非常適合這裡生存,能盤住沙漠,我們就尊重這一自然規律,學習老祖宗,再也不能像過去那般隨意破壞、掠奪了。”
鐵山這代人俯瞰著眼前1.2萬畝“山水工程”實施區域,有一種父輩欠債他們來還的氣概。2023年,正值春季大風季節,白毛風昏天黑地,凍土地還沒有完全解凍,漫山遍野都是攢動的人群。鐵山他們頂風冒寒,揮鎬刨開一層層凍土,挖坑栽樹苗,澆的也是帶冰碴兒的水泡子水,人一張口,嘴裡灌滿風沙說不出話來。科爾沁沙地原本有植被覆蓋,地下水位高,沙漠本身就是蓄水池,栽種的灌草容易成活,眼下已蔚然成片,布滿沙野。他們現在面臨著新苦惱,就是如何管理保護好正在綠化的項目地。
農牧民以養牛為主要經濟來源,需要大量青儲飼料,有些人仍習慣性地把牛放進沙坨子裡,免不了啃食項目地樹草。旗政府加強監管,同時成立禁牧大隊進行巡查,違規放牧就罰款。
我問鐵山書記,你家有幾頭牛,挨過罰嗎?他尷尬一笑說,有40多頭牛,有一次牛撞壞圈欄跑出去進了沙坨子,被罰了款。我問旁邊的護林執法組長白音嘎,是真的嗎?他說當然是真的,領導犯錯,更得嚴罰!
二
告別敖倫嘎查,我們奔往寶格圖嘎查,尋訪一個人。他叫白銀山,庫倫旗自然資源局干部,全旗“山水工程”主要負責人。在寶格圖嘎查紫花苜蓿草場,我們見到了他。白銀山畢業於內蒙古農業大學,是種草治沙的行家。他開口就訴苦,說服農民改變原有的耕種習慣太難了!這村7000畝紫花苜蓿草場是他們用一冬時間苦口婆心說服,才播種成功的。
我們眼前鋪展開一大片綠油油的苜蓿草,一望無際,馬上可以收割一茬兒喂牲口了。老白說,長出新一茬兒后,又可作青儲飼料,一年可割三茬兒。紫花苜蓿是薔薇目豆科類多年生草本植物,作為世界各國廣泛種植的優質牧草,產量和營養價值都比苞米秸稈高。經老白他們普及知識、循循善誘后,全旗種下兩萬多畝苜蓿草,既能治沙又能增加收入。白銀山很是欣慰,一臉倦態全淹在笑容中。
庫倫旗“山水工程”另一重點地區在塔敏查干流沙帶中東部,即瓦房牧場所屬流沙區。該牧場土地面積4.6萬畝,大多是流沙帶坨子加上小片窪灘耕地,屬科爾沁沙地庫倫旗中心地帶,現在1.5萬畝寸草不長的流沙坨子已列入“山水工程”。通遼市要殲滅的100多萬畝科爾沁沙地,庫倫旗境內就達44萬畝,時間緊、任務重、壓力大,工程採取的主要技術是草方格固沙治沙。
瓦房三分場黨支部書記阿榮開一輛大功率越野吉普,載著我們呼啦啦駛過一座積水涵洞,再嗚嗚吼叫著爬過一座座高陡沙梁,沖過低窪沙坑,終於把我們送到十公裡外的一座荒漠沙峰上。阿榮30多歲,有勇有膽識,車技也好,黑胖矮敦的身體內似乎蘊藏著無窮力量。隻見他的紫紅臉上露出白白牙齒,抬手一指說,看吧,草方格像天羅地網,鎖住黃沙,真壯闊呢!果然眼前茫茫沙海坦蕩遼闊,舉目望,草方格布滿四周,向天際擴展。許多人正在草方格裡忙活,黑黑點點如螞蟻搬家,有人開壟溝,有人埋干草,后邊跟著強力壓土機轟隆隆地夯壓加固,呈現出一幅沙場秋點兵,萬裡戰猶酣的繁忙景象。
阿榮說,在春天,風沙中剛埋下的干草不小心就被大風拔起刮走,追都追不著,遇上沙塵暴更危險,人都有可能被卷走迷失於大漠之中。這時見不遠處的沙梁上,有一位婦女正抱著一捆干草去埋方格,突然一陣大風吹來,她一個趔趄,風刮走了她包頭的紗巾和懷裡的那捆草。隻見那婦女並沒有去追擋風遮臉的紗巾,而是拔腿就追那捆正嘰裡咕嚕滾走的干草,人也連滾帶爬,歪歪斜斜,跑出幾十米,追回那捆草才綻放出笑容。這時她那條包頭的藍色紗巾,被卷到高空中,好比一隻美麗的沙鷗在飛翔,悠悠蕩蕩。
三
菩提,梵語為覺悟之意。因佛祖在此樹下頓悟而被稱為覺悟樹。庫倫北部敖倫林場的莽莽沙坨裡,居然生長有近3000棵菩提樹,與老榆樹、山杏樹、五角楓等原始老樹種組成一道阻擊風沙的有力屏障,如一群老戰士頑強奮戰在治沙第一線。
十多年前,塔敏查干流沙帶深處,跋涉著一個疲憊不堪的中年人。他叫初永軍,旗林業總站副站長、高級工程師,正帶領助手普查沙漠樹種,為治理科爾沁沙地提供第一手科研資料和適合治沙的林草物種。烈日炎炎,百裡流沙如大蒸籠,酷熱難耐,轉眼間就把人身上一點水分蒸發掉。四周茫茫沙帶上不見一棵綠色植物,初永軍站在一座沙坡上觀察,突然聽見一頭驢嗚哇嗚哇玩命的嘶叫聲,看到沙漠裡有一頭大黑驢正拼命追趕一叢“綠草”。而那叢“綠草”是活的,能移動,正驚恐萬狀地躲避黑驢的追擊。原來,那“綠草”是長著兩條腿的大活人,一位穿著一身綠色軍裝、背著綠色背包的復員軍人。他呼哧帶喘地躲在初永軍他們身后,萬般不解地問:“這頭驢是瘋了嗎?它為啥追我?”初永軍吧嗒著干裂的嘴唇苦笑著答:“可憐的毛驢兒遠處見你一身綠色,誤認是一叢綠草,要啃一口啊!百裡黃沙一點綠,打遠看別說你還真像一叢綠草,這頭驢是太想吃到綠草了!”那位軍人喃喃自語:“這也太恐怖了,我家就在前邊敖倫屯,沙化太嚴重了。”這位名叫鐵莫的復員軍人,回家后放下背包,投身治沙事業,后來成為一名治沙勞模。
初永軍就在黑驢追人的不遠處,發現了第一棵菩提樹。這棵樹悄然屹立在一座沙丘上,枝葉濃綠茂密,樹皮粗粝堅硬,半腰樹皮上自然形成長方形如藏經般的神秘紋路。一生與草木打交道的初永軍,認出此樹喜出望外,從切片上測出至少有800年。菩提樹能在科爾沁沙地生存,這是生命的奇跡。初永軍受到啟發,如果能夠培育出菩提樹種子,在科爾沁沙地廣泛推廣栽種,與錦雞兒、紫花苜蓿、山杏等形成喬灌結合的立體治沙防護體系,豈不更好?百姓視菩提樹為吉祥樹,會喜歡種,也不會傷害砍伐它們。
初永軍說干就干。菩提樹種子休眠期長,育苗難度大,需要打破內外休眠期。老伴見他把自家冬季儲存土豆白菜的倉房騰出來,搬來好多泡沫箱開始鼓搗,很不解,問他這是想孵雞仔嗎?他回答:“不,比雞仔更珍貴,我要孵化菩提子兒!”零下30攝氏度的大雪天,他從外邊用雙手捧來一盆盆白雪,倒進泡沫箱裡,手和臉凍得通紅。然后用沙土配置營養土,和冬雪一起攪拌均勻,埋入種子,再抱來家中厚棉被緊緊包裹住,定時監測。兒子笑言:“老爸你這不是育種,是坐月子!”老初微笑說:“坐月子才一個月,我的菩提樹種需要一冬一夏再一冬,共兩冬一夏才可孕育成活!”
初永軍一邊在家裡孕育菩提樹等治沙樹草幼苗,一邊在野外勘查作業,馬不停蹄,各種治沙和生態修復工程中常常見到他的身影。初永軍帶著團隊一年四季奔波在治沙線上,春季大風能見度不足30米,夏季高溫地面溫度高達四五十攝氏度,他們扛著測量儀器爬沙包沙梁,擺腳架搖旗吶喊,嗓子啞得說不出話來。背著沉重儀器走幾十公裡,餓還可以挺住,口渴就難以支撐,哪怕見到牛蹄坑裡的泥水,都拼命吸飲。有一次沙漠裡苦干60天,沙塵暴卷走了他們的帳篷,初永軍死死捂住測量儀器和項目數據,差點被埋在幾米厚的流沙下。
科爾沁沙地治理第一線,聚集著眾多像初永軍這樣的技術專家和實干家,他們與受沙苦已久的廣大民眾一道,投入這場治沙行動。如今,初永軍的菩提樹苗圃已經蔚然成林,將用於治沙。打好科爾沁沙地殲滅戰,徹底治理本旗境內40多萬畝沙地,這是擺在庫倫人眼前艱巨而光榮的任務。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遠,曙光就在前邊。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1月04日 第 07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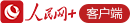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