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壯闊的歷史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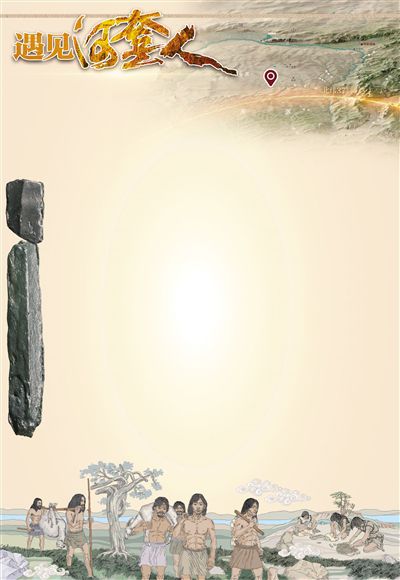
薩拉烏蘇遺址

薩拉烏蘇遺址出土的石器。

薩拉烏蘇遺址出土的石器。
鄂爾多斯高原,黃河中上游“幾字彎”中的璀璨明珠,自古以來,這裡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地帶之一。
薩拉烏蘇河,蜿蜒於鄂爾多斯高原,發源於陝西白於山,黃河一級支流無定河的上游。
數萬年前,“河套人”在薩拉烏蘇河畔繁衍生息。之后,距今千百年來,波瀾壯闊的黃河文明在這裡勾勒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發展脈絡。
相融共生的故事,從這裡講起。
連續演化 一脈相承
薩拉烏蘇,位於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無定河鎮西南部,美麗如世外桃源。
距今10—5萬年前的薩拉烏蘇也很美:黃沙碧水、深谷清流,水草豐茂、生機盎然,蒙古野驢、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在草原上或靜靜覓食或奔跑嬉戲。
1922年至1923年,法國地質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德日進在薩拉烏蘇採集到了大量石器、動物化石以及骨角器、動物碎骨等遺存,其中,包括一枚中國發現最早的古人類牙齒化石“鄂爾多斯牙齒”(即“河套人”的牙齒)。
20世紀20年代,桑志華除了在薩拉烏蘇發現了舊石器外,在甘肅慶陽、寧夏水洞溝等地也發現過。
這些發現石破天驚,打破了國外考古學家認為中國北方黃土層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遺跡的判斷,從而奠定了中國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基礎,並使中國在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上佔據了重要國際學術地位。
1924年至1928年,桑志華、德日進以及法國學者步日耶、布勒等人,就此陸續發表文章與專著,向世界公布了這些重要考古發現,並大膽推測:“在舊石器時代中國的古人類可能屬於一支規模很大的人群,這支人群不止一次形成遷徙的浪潮,向西到達歐洲。”
這些材料與論斷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薩拉烏蘇因“河套人”的牙齒而備受矚目。由此,薩拉烏蘇走出烏審旗,走出內蒙古,走出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符號。
薩拉烏蘇等遺址出土的文化遺存延伸了華夏人類生存與演化的歷史,其后百年間,更多實証中國百萬年人類史的舊石器時代遺存被發現:北京猿人、山頂洞人、泥河灣舊石器時代遺址……
根據這些持續不斷的發掘研究,証實在舊大陸的東方古人類間,存在著石器技術和文化上的交流與延續。
“薩拉烏蘇的石器用打擊技術制作,屬於在中國北方長期流行的小石片石器體系,具有明確的技術淵源和傳承關系。這一文化傳統約170萬年前初現於河北泥河灣盆地,約7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延續了這一技術體系,直至數萬年前的‘河套人’、山頂洞人等都在制作和使用這種工具。”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亞洲舊石器考古聯合會名譽主席高星說,這些石器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精細化和多樣化,但是技術、類型與組合一脈相承,表明華夏大地的先民是連續演化、薪火相傳的,可以循跡追溯東亞現代人(黃種人)的祖先。
高星說,到如今,中國境內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有2000余處,構建和書寫了東方故鄉200萬年的人類演化史。
相融共生 文化互鑒
百年間,專家們在薩拉烏蘇遺址厚厚的地層中,除發掘出土了小石器、動物化石等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外,還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石鏃、宋元時期的黑釉片、陶片以及清代的銅錢等歷代文物。這表明,繼“河套人”之后,鄂爾多斯高原這片土地上一直有人類活動。
《烏審旗文物志》記載,至今,烏審旗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至夏商時期的遺址,漢、北魏、隋唐等時期的墓葬,宋代、西夏時期的錢幣窖藏,唐、西夏等時期的古城遺址以及清代的古寨、石窟等豐富的古代遺存。
“綜合歷史遺存和文獻記載可知,秦漢以來,鄂爾多斯高原從事農墾的人群與游牧的人群相互之間交往活動比較頻繁,南來北往、東西遷移,雖有紛爭,但和平交往、相互借鑒、交流交融成為歷史發展主流。”烏審旗檔案史志館退休研究館員郝繼忠說,秦漢時期,中原大批移民來到鄂爾多斯高原,掀起了多民族匯集的浪潮﹔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等北方民族南遷,多民族交往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匈奴鐵弗部首領赫連勃勃按照中原王朝的模式建立的大夏國,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
6月6日,毗鄰烏審旗的陝西省榆林市靖邊縣,統萬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開園。園內,殘缺的城垣、隅台和馬面等夯土建筑,依稀展現出1600多年前大夏國都城統萬城的真顏。
公元407年,赫連勃勃建大夏國,公元413年至公元418年,他在當時水草豐美的鄂爾多斯高原建起統萬城,因城牆為白色,當地百姓又稱白城子。
作為鄂爾多斯高原唯一的古代都城和現今世界上發現的唯一匈奴都城遺址,建成后的統萬城堅固挺拔,高大宏偉。《晉書·赫連勃勃》中如此形容:“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裡。”﹔而城裡,又是一派“華林靈沼,重台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的華美景象。
郝繼忠說,隨著居住日久,習慣定居生活后,赫連勃勃依托無定河,開發了大量農田,統萬城成了亦牧亦農的塞上江南。
在各民族長期遷移往來中,修建於秦始皇時期的秦直道始終發揮著交通、商貿、移民等方面的作用,同時也成為了民族融合的大通道。
“秦漢以來,中原政權和北方游牧民族對貫通鄂爾多斯高原南北至陝西關中地區的秦直道等大通道極為重視。”郝繼忠說,歷代經略,統萬城及鄂爾多斯南部地區成為各民族在大通道上南來北往、東進西出的重要節點,促進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據研究,西漢“昭君出塞”也走過秦直道。
秦直道南起陝西省雲陽縣,止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九原區,全程700多公裡,被譽為“古代高速公路”。
文明沃土 豐潤精神
鄂爾多斯高原這片熱土,數萬年前,“河套人”辛勤勞作、以啟山林。之后,距今千百年來,中華各族兒女在此生生不息、繁衍壯大,把火熱的生產生活實踐鐫刻成歷史、積澱成文明。
橫亙鄂爾多斯高原的薩拉烏蘇河,綿延流淌,將先人開拓拼搏、百折不撓、團結奉獻之精神浸潤進鄂爾多斯高原每寸肌理,承載著中華民族磅礡自信的基因和血脈。
烏審旗無定河鎮巴圖灣村,緊鄰陝西省靖邊縣,是薩拉烏蘇生態旅游區的一部分,上游30公裡處,是薩拉烏蘇遺址﹔下游5公裡處,是統萬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村中,薩拉烏蘇河水緩緩穿村而過。
這裡的歷史波瀾壯闊。
1935年5月,紅軍22支隊解放巴圖灣。為了保衛鄂爾多斯成立的第一個鄉蘇維埃政權——巴圖灣鄉蘇維埃政府,當地青壯年成立了巴圖灣赤衛隊(即巴圖灣民兵連的前身)。隨著革命形勢不斷發展,這個曾經維系一方安寧的力量,逐漸成為守衛陝甘寧邊區北大門的重要武裝力量。
紅色火種在巴圖灣點燃,巴圖灣民兵檢查站遺址、1949年秋后中共烏審旗委辦公舊址、中國共產黨納林河小組谷家灣舊址等保存至今的革命文物,見証了那段烽火連天的崢嶸歲月。
一灣見証一旗,一旗映射一市。
截至目前,烏審旗是鄂爾多斯市36處革命文物遺址分布最多的旗(縣),全市有7處納入自治區革命文物保護名錄,烏審旗就佔3處,其中包括1949年秋后中共烏審旗委辦公舊址。
烽火歲月,鄂爾多斯地區各族兒女萬眾一心跟黨走,不畏強暴,奮起抗爭,譜寫了一曲曲氣壯山河的革命凱歌,激勵一代代后來者接續奮斗。
69歲村民白治文的父親白玉德,曾是巴圖灣民兵連的一員。從小聽父親講革命故事的他,血脈裡植根著深沉的家國情懷,從2017年至今,他已在1949年秋后中共烏審旗委辦公舊址擔任了6年義務講解員,滿懷激情地把父親講給他的故事講給一撥撥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齡的參觀者,使紅色精神代代相傳。
現在,巴圖灣村圍繞1949年秋后中共烏審旗委辦公舊址、巴圖灣民兵檢查站遺址、烏審旗革命故事講習館等“三址三館”,建成了巴圖灣紅色文化小鎮,更多的人可以來此接受紅色教育、錘煉黨性。
“小鎮通過文獻照片、場景復原等,生動再現了鄂爾多斯地區紅色革命的奮斗歷程。”烏審旗無定河鎮黨委委員、宣傳委員達布拉汗說。
回望來時路,鄂爾多斯高原承載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脈,歷經千年風雨依然璀璨奪目﹔再看今朝,文明悠長、日新月異的鄂爾多斯高原必將見証更加輝煌燦爛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記者 周秀芳 劉春 於海東 高瑞鋒)
(圖片由記者 於濤 懷特烏勒斯 孟和朝魯 攝)
(手繪長圖:蘇昊)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